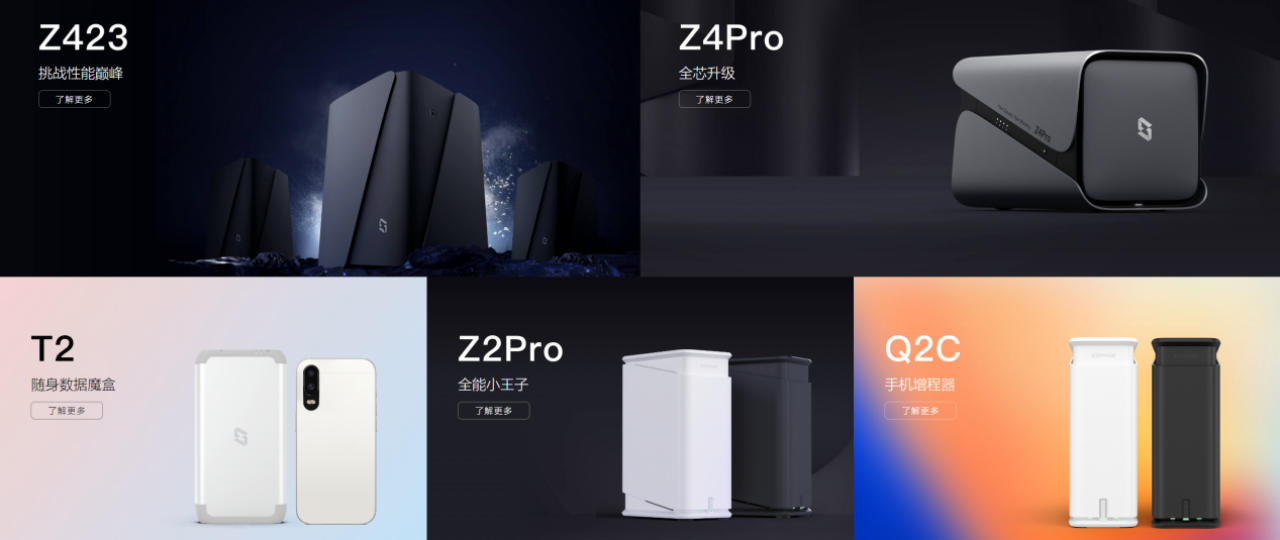摘要: 9月29日,“大师·对话”活动“银幕游历者——米格尔·戈麦斯大师班”在平遥电影宫内门厅举

9月29日,“大师·对话”活动“银幕游历者——米格尔·戈麦斯大师班”在平遥电影宫内门厅举办。活动由选片人、策展人、作家、导演马克·佩兰森主持,导演、第八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费穆荣誉评审主席米格尔·戈麦斯围绕电影的虚实问题与观众分享他银幕游历的经历。
延伸阅读:导筒专访米格尔·戈麦斯:戛纳主竞赛口碑之作,穿越历史与现代、虚构与真实的壁垒
您是如何进入电影行业,如何有拍电影的想法的?因为您的电影当中总是有着一份童真,拍电影是不是您幼年或者少年时候的愿望呢?
回到您刚才的问题。我怎么入行的?很像正常的路径,一开始我在里斯本上的戏剧电影学院,我不是一个好学生,甚至高中的时候看了太多的电影,没有更勤奋刻苦地学习。我当时学戏剧学得不太好,所以让我学制片。但我这个人组织观念不是太强,所以不太善于去组织协调,谁都不想让我进组,也不想给我指派差事,连送咖啡都不要我,所以我是毕业即失业,也不知道以后将何去何从。
正好有朋友在报纸工作,他说要不你写写影评吧,所以我说那试试看,于是就去写影评,写了一阵子以后,我以辛辣的笔法而著称,所以小有名气,后来我就申请政府的资助来拍短片,最后也成功了。为什么呢?就像电影行业的人想让你拍部电影给他们评论,给你上一课,当时大家想看我的笑话,希望我上来就拍一个烂片,我也让他们如愿了,我确实第一部的短片就是一个烂片,好在是没有引起什么人注意,所以我也算逃过去了。
您是从写影评开始,后来您拍片我也注意到,会时不时引用到别的电影,包括像《禁忌》或者《Entretanto》、《壮游》这样的电影,里面会有其他电影的身影。您拍片的时候是有意借用、化用,还是您特别专心做您的电影就已经忘了这些细节?
一开始我们在拍的时候就会忘掉其他电影,我们做决策的时间往往就是拍摄的时间,而你拍摄必然会拍你面前具体有形的东西。是人也好,是物也好,不可能拍的是一无所有的东西。电影记忆已经成为了我的一部分,可以说非常重要,虽然说不一定有我的真实生活体验那么重要,但是这种重要性可以说是等量齐观,另外也有其他的艺术门类,像音乐等等。
另外,像《绿野仙踪》,不仅对我个人来说是一段难忘的回忆,对于大家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甚至所有的电影都是以往电影的一种翻拍。《绿野仙踪》堪称电影中的电影——在堪萨斯州乡间生活着一个女孩、一条狗,龙卷风袭来把女孩带到了一个叫奥兹的地方。1930年代美国的这部影片是在电影棚当中拍的,但是通过奥兹这个地方,反映出来也是现实,奥兹世界的规则与现实世界完全不一样,甚至物理定律都不一样,世界千变万化,与我们现实形成了一个平行的宇宙。我的电影也是希望能够呈现堪萨斯州这样的现实世界,并且构建像奥兹这样的虚拟世界,试图让现实和虚幻的世界能够去形成对话。所以具体去拍的时候,不会拘泥于刚才我所讲的这些东西,而是让镜头去讲话。
能不能谈谈您具体在拍片的时候有什么一定之规?您拍片不可能思路天马行空,镜头什么都拍,一定会有一些取舍,有没有什么规则存在,甚至说所有影片都是吾道一以贯之,还是会因影片而异?
我拍片的时候规则也会有所调整,甚至说在一部电影里面就会有调整,我有的电影是分上下部,就是因为其中各自适用的规则是不一样的。在影片和观众之间实际上是有权力关系的,给予电影的权力或者力量,我觉得过多了,使得观众有时候会感到无助、茫然,这样观众就陷入被动的地位。所以我把电影分出上下部,虽然说这种方法并不一定能够适用于所有人、所有影片,但是能够激活观众,让他们变得更加主动。
比如我第二部长片《可爱的八月》,上半部我在拍片的地方希望去拍摄人们的肖像以及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试图把电影完成。后来到中段的时候,这些一开始出现的人就处在虚幻的现实当中,在他们的仪式之后开始描绘虚拟的世界,而此前在现实当中采集的元素会在虚拟世界重现。我的这部影片并不是只有第一和第二两个部分,还有第三个部分,因为我希望给到观众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在脑子里面形成这部电影的第三部分。
在观众的记忆当中,第一部上半部出现的这些人物,能够透过头脑连点呈现,跟第二部虚幻世界当中串联起来,比如第一部出现的人物在第二部的虚幻当中已经换了名字,但是观众能够把这个空余补上。《可爱的八月》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为我赢得了奖项,影片获奖也使我获得一笔创作资金,能够让我主动开展以后的创作。
而本来这部电影最初没有像我刚才描述的方法去拍,而是按照比较经典的结构去拍摄。在开拍前的两个月,制片人找我说,咱们的电影没钱,要不然你再等一年,我再筹点钱。后来一直是商量了三天,我当时也很灰心,但是最终我没有想着等着钱到位,因为往往资金等着等着就半途而废了。所以我就想不如找个摄影机,建一个小的摄制组,拍一个精简版。但这也改变了我,后来当然也不断获奖,得到一些奖金,但是我们也要能够做出反应、进行调整。葡萄牙后来遇到了财政危机,在2013年的时候,国家的经济濒临破产,欧盟要求国家采取紧缩措施,所以对于社会和人民来说要过紧日子,我们的影片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为了危机做出反应,要去通过拍摄虚构的世界去做回应。如何能够把虚幻世界拍得栩栩如生,针对现实世界的困境做出反应,我们请了一些记者,给他们提供办公室,每天去搜集新闻,看看现在葡萄牙在发生什么。
我和编剧根据整理出来的新闻来编写剧本,把这些故事尽快拍出来。我们也有很优秀的摄影——一个很著名的泰国摄影师。我们也和阿彼察邦、瓜达尼诺都合作过。当时他们受邀到里斯本住了一年,相当于伴随着记者的采写过程,摄影师也和整个组一起,在一年的时间里不断地拍摄。
您原本想拍《腹地》,本来2020年左右打算在巴西拍摄,但由于地区出现了危机,导致您改去拍《壮游》。能不能在这个方面跟我们谈一谈,是不是您每部电影都是应因危机而产生的?
因为巴西那边有危机,所以影片无法完成拍摄,我是希望它能作为我下一部作品拍成,因为毕竟现在巴西的政治氛围已经不同于以前,而且《壮游》也在戛纳为我赢得了奖项,所以希望能够有助于我未来拍片。
拍摄《壮游》的想法是在我筹拍巴西那部电影的同期产生,但是与它没有关系,《壮游》的灵感来自于毛姆小说《客厅里的绅士》当中的两页纸,里面描绘了主人公在缅甸的游记和旅行当中的经历。当时游记写的是主人公在缅甸的所见所闻,比如市场、庙宇、城市、丛林等等,是一般游记当中常见的题材,同时记录了他的际遇。他在曼德勒见到了一个英国人,这个英国人给他讲婚姻当中的经历。这位男士和一位女士订婚已久,但最后没有结婚,因为当时女士来找他结婚,男的就逃婚了,之后女士就在一直追他。因为他们是1918年在英国领事馆结婚,所以我们想调档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历史记录。
后来研究发现这件事并不存在,而是虚构的,甚至是一种反讽,即男人是懦夫,而女人很顽强。这是不够拍一部电影的,撑不起来,我们以此做故事的基础,让主人公不断在各个国家之间一个跑一个逃,这位女性不断地说“我要来了,我要来了。”这就是电影的故事梗概,但是我们想一部电影也不止是一部故事,所以我们用电影讲故事的时候,不止是你头脑当中有了一个影像你就可以去讲,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催促你去讲。
如果说你电影别的没干,只是讲一个故事的话,人家还不如读小说,所以我们要用电影形成一种可信,让观众能够获得多重的体验。因此《壮游》其实是两个故事叠加在一起的,前半部分主要是讲男人的逃,后半部分主要讲的是女人的追,整个电影不管上半部还是下半部,都是把现实与虚构的世界相融合,就像把堪萨斯州和奥兹世界相融合一样。这些影像里就包括主人公所去往的各个国家,其中也包括中国。
电影在风格上的冲撞表现为像奥兹和堪萨斯州的对立,现实和虚幻世界的对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现实拍出来比奥兹还像奥兹,现实变得像超现实一样,这是电影的魔力,通过电影来形成过滤和升华。现在面临两种非常不同的影像类型,也就是现实和影棚,我们并不是为了重现1918年的景象,就把那些现代的元素从我们的现实当中抹去或者隐藏起来,而是通过我们的编剧以及剪辑能够让这些元素形成连贯的感觉,即使屏幕上没有人物也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至于说一个观众心目当中,电影人物是一直存在还是断断续续存在等等,这就是取决于观众自己的解读了。在我拍的过程当中,我一直都不知道这样拍行不行,能不能行得通。
另外一部电影《禁忌》也是分两部,一部分是在里斯本,另外一部在非洲的莫桑比克拍摄。在第二部非洲部分里,我们是听不见对白的。虽然有旁白,而且观众可以看到影像当中人物的嘴在动,却听不到他们说什么。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因为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这样做很难。《壮游》也是在影棚当中重现1918年的情形,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能行得通,但是只有一种办法能够去验证这个是不是能够行得通,就是把电影拍出来看。
在《壮游》当中您对于现代世界也是采用了旁白的形式来表现,讲述主人公的跨国旅行。我想问顺序的问题,您在拍的时候旁白就已经胸有成竹了呢?还是在拍完之后,甚至剪出来之后再去加旁白?
很好的问题,马克,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谁先谁后的问题,我之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先去拍摄,然后采集了大量的素材,拍了很多的镜头,最后形成了一个素材库。我们当时拍的时候是没有旁白的,也是找了一些老素材,比如说能够了解到当时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把一些老电影、老镜头嵌入到我们现在的影片当中去。比如我要还原30年代,我就找30年代在当地环境下拍摄的旧影像,把它用到我们现在拍的电影里面,而且不止融入过去的影像,同时也包括我们要塑造未来的影像素材也会加进去,以及在当代的中国、日本、越南、新加坡、泰国和柬埔寨拍的这些素材。因此在一开始并没有加旁白的想法。
我跟你说过,总有那么一刻制片人会告诉你,咱们没钱,因为危机一直存在,一直在延续,我毕竟已经拍了25年,我已经习惯于危机会接踵而至,我就期待着,预测着它就会来。虽然不知道哪天来,哪个月来,但是我知道一定会来,另外像棚拍成本也是非常之高的。
Q1:首先感谢您的电影给了我很多灵感。第二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谈到过电影和观众之间的权力关系,您也是希望能够把观众化被动为主动,我们也知道现在除了观看电影以外,观众也被其他媒体消耗注意力,在这些方面你是怎么来处理的呢?
我之前讲到说,我觉得我们银幕这一端权力太大,观众那一端权力太小。准确来讲,一部电影可以命令一个观众,或者说教一个观众,说你应该现在有这样这样一个感受,你应该觉得这个人是好人,那个人是坏人等等,这样在各个方面全盘受到电影控制的局面之下,观众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弃剧而去,走出影院。
我越来越觉得影片有义务为观众创造空间,就像建筑艺术一样,建筑艺术无非打造一个空间去设想人们如何进入、如何在这里面生活、如何来体验,我们电影也是需要给观众们营造这种体验。但是营造观众空间的方式不能一刀切,一种经典的方式就是创造对立,可能同样的场景在有些人心目当中就是喜,而在其他人眼中就是悲,这种模糊不定赋予了观众空间,让观众可以自行判断。如果一个场景只有一种解读的话,就没有给观众提供选择权,而两个选择总好过一个选择。例如《可爱的八月》在第二部当中是让村民去扮演这些角色,到底这个人如何来定位、定性,大家可以自己来判断,观众可以把他们视为角色,也可以把他们视为扮演角色的村民。
Q2:您好,想请问一下《壮游》这部电影当中,色彩交替的部分是如何实现的,您的逻辑是什么?什么时候使用黑白,什么时候使用彩色?
确实在《壮游》当中90%的篇幅是黑白,10%是彩色。我们是用胶片拍摄,但是黑白胶片的感光度不够,为了拍一些夜戏和内景我们也带了少量的彩色胶片,但这些部分当时最初的计划也还是把它转成黑白一起来剪辑,所以剪辑过程中大部分还是黑白胶片拍的,彩色胶片部分也转成了黑白一起剪,剪着剪着,大家觉得想看一下还原成彩色效果怎么样,放起来很漂亮,所以就是目前的设计。
Q3:您刚才回答第一个问题时说到您的影片营造一种空间感,假如您给了观众两个选择,向左或者向右,您对选择是否有偏向性?如果有的话,您对于偏向性又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要创造空间,但并不是随机给出选项。我们设计出来的空间并不是任凭观众可上可下,可左可右,东西南北随便变的,我们是设计出来倾向性的选择。对于导演和制片来说,如果大家无从去选择左还是右,或者只有一个选择的话,那就是一个坏消息了。如果观众看完后觉得不喜欢,我们会觉得这就是生活,我可以接受,毕竟人人各有不同的好恶,希望这回答了您的这个问题。
9月28日上午,第八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大师·对话”活动“关锦鹏——人在香港”于平遥电影宫内“站台”露天剧场举办。
第八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大师·对话”系列学术活动由劳力士ROLEX大力支持。本场活动由第八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评审主席、电影导演、制片人关锦鹏主讲,影评人、翻译家、电影制作人、策展人汤尼·雷恩主持,两位围绕城市发展、文化认同、香港电影市场变迁等问题展开畅聊。
你小伙子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你,我听说你开始是有志于演戏,而不是导戏,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因为我念的是香港的一个中学,叫“培正”,很有名。像王晶导演,女演员黄杏秀,都是我的师哥师姐。学校有一个户外活动的剧团,我被挖去担任幕后,有些时候弄弄布景,有时候被邀请去饰演一些小角色,结果我发现我自己蛮喜欢表演的。我念完中学,在浸会大学读传理系的时候报名了无线电视的演员训练班。我从进训练班以后开始学表演,但训练班是一年的课程,到差不多结束的时候要参加表演,哪怕是一些小角色,也需要去参加。结果当我自己有机会看到自己演出的时候,我觉得我非常不上镜。哪怕饰演一个小角色,焦点还是会在自己的脸上。后来我就觉得,这不对,我是不是真的继续应该做演员呢?碰巧那个时候无线电视的总监找我过去,说:“关锦鹏,虽然你在训练班的成绩很好,但是我也觉得你好像不太上镜,对吗?”我说:“是,你太懂了。”
那个时候,无线厘米拍电视剧的一个群体。那个阶段有很多大家认为很棒的导演,包括许鞍华、谭家明、徐克、章国明等等。所以我就被安排做幕后工作,比如幕后的场记、助理编导。说实在话,我在他们的身上学到很多。并不是因为他们跟我说应该怎样拍戏,他们也从来没有这样,只是在现场帮他们做场记、助理编导和副导演的时候,通过观察他们怎么演员,怎么跟摄影师沟通,就让我得到了非常好的学习。我开始慢慢觉得,给自己带来满足感的是拍电影而非当演员,这种感觉非常棒。
后来到80年代初,整个电影环境非常好,这一些导演都被邀请到电影市场来拍长片,因此形成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这就是当时的香港电影新浪潮,包括许鞍华、谭家明、章国明、徐克、严浩等等,我就跟着他们当副导演,从此我就没有离开过电影行业了。
我一开始是想当演员,但是我很感恩后来让我碰到这些导演,有机会从他们身上学习到,然后参与电影做副导演,后来1985年,有老板愿意说:“诶,关锦鹏,你自己试试当导演啊?签一个合约,剧本慢慢弄。”就这样,我在1986年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女人心》,由周润发、钟楚红、缪骞人出演。那时候我28岁,时间太快了,今天算一算距离都将近四十年了。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在1981年拍《投奔怒海》,当时你给许鞍华做助理导演。那并不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但是是我第一次来到像湛江这样的中国内地区域。作为一个新导演,像徐克和许鞍华,之前都在国外学习电影,但回到香港之后却没有电影可拍,像邵氏等等这些大厂也不太愿意跟这些年轻导演合作,所以他们一开始从电视开始拍,你也是如此。像你,以及更前辈一些的徐克、许鞍华这些人代表了一代人,也代表了香港影坛巨大的变化。之后你可能也见到一些其他的导演,以及其他的影人,开始一个新的类型创作,可不可以就此谈谈。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看电影,那个时候有很多大公司,像邵逸夫的邵氏电影公司,还有邹文怀的嘉禾等等,投资环境非常好。但是香港电影工业在某个程度上是商业性的,所谓的商业性是指走类型电影道路。比如说,八、九十年代有很多类型电影,像黑社会电影、爱情电影、喜剧、悬疑电影等等。许鞍华的第一个电影叫《疯劫》,看似是悬疑类型的电影,但是实际上讲了一个非常动人的爱情故事。所以不管是在无线电视也好,还是后来当他们的副导演参与电影工作也好,我们都很清楚香港电影在某些程度上的工业性,但是你可以有你自己拍电影的风格。
从某种程度上讲,许鞍华、谭家明这些导演,让不光香港本地的观众,甚至亚洲其他地区,韩国、日本,甚至更远一点的欧洲、美国等等,都认识到香港电影新浪潮。我想非常感恩地说,是新浪潮给我们这些稍晚一点才开始、在80年代中拍电影的导演提供了机会,那时真的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相比今天一些香港年轻导演:比如我最近监制的《但愿人长久》,导演所拍的算是她的半自传,她自己也是在97年从内地移民到香港,在香港生活,电影说的是她跟她家里人,父母、妹妹的关系。在八、九十年代,大家都很清楚香港电影工业是要类型电影,而现在,很多年轻导演更愿意拍他自己非常个人的电影,这在对市场的冲击上是有差别的。
你讲得很对,确实,年轻人们总有各自不同的追求,但是共同点是希望不要自我重复,而是求新求变。包括更多使用实景而非棚拍,更多使用现场录音而非配音,这可能来自他们之前拍电视剧的习惯,但却改变了整个香港电影的风格和感受,不管是像徐克的古装片《蝶变》还是你的时装片《女人心》,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的确,从无线电视把他们都招到制作组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用16厘米来拍电视剧了。不同于一般在棚里拍VCR的样子,所有的东西都很生活化,包括整个场地、演员的表演,以及声音。即使类型不同,但可以感觉到人物是在生活,这是有别于过去一些电影或电视剧的。这也让观众耳目一新,这些电影既有剧情,又能感觉到那些导演自己个人非常强烈的风格和想讲的故事。我非常感恩无论是在无线电视当幕后副导演,还是跟他们拍电影做副导演的经历。那时候的环境,不仅培养了香港的电影人,还培养了一大群观众对香港电影的爱。
你的第一部影片是给传统的大型电影公司邵氏拍的,但是你那部影片跟邵氏早年的典型片子非常不一样。打入历史悠久的传统电影公司去拍一个风格很不一样的影片,你有没有受到公司以及工作人员的呢?
虽然资金来自邵氏,但我很幸运的是,当时找我当导演的是珠城电影公司的老板梁李少霞女士,那时她已经投资了电影,包括章国明的《点指兵兵》,麦当雄导演的《靓妹仔》。所以这个公司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个人风格,非常鼓励年轻导演在公司制作自有风格的影片。哪怕资金确实来自于邵氏和嘉禾等大公司,珠城电影公司的老板也站在前面帮我们挡了很多,发挥了很多她作为制片人该做的工作。某个程度上,香港电影新浪潮也非常感谢这位女士。
《女人心》是你唯一一次跟邵氏合作,之后你就独立创作,跟各家电影公司合作,包括为自己的电影公司拍片。当时80年代的时候,你的雄心壮志是什么,当然我们看电影也能够看出来,但还是想请你谈一下优先拍什么样的电影。
我第一部电影是邵氏投资的,由周润发、钟楚红等人出演。剧本比较偏商业化,讲丈夫有外遇,是部蛮轻松的喜剧片。结果那一年票房相当好。接着我的第二部电影是由珠城电影公司给我投资,还是找的大明星周润发、梁朝伟等人出演,但是剧本却非常不商业化。那个时候香港的排片不同于现在,那个时候排片时间是固定的,有中午的十二点半,下午的两点半、五点半,晚上的七点半、九点半。其实要是老板想知道当天的票房预估,下午两点半就会有一个数字可以预估整天的票房。《地下情》上映的时候评论很不错,但是老板下午两点多打电话去问票房,得到的票房数字非常不好,他就说:“算了,帮我拉下来,不要上了,丢脸。”所以《地下情》是我的第二部电影,评论不错但是票房不好。
接下来,我被邀请去了嘉禾电影公司,叫我拍李碧华的一部非常受欢迎的小说《胭脂扣》,电影也有梅艳芳、张国荣这样的大演员加持,基本上造就了商业化的可能性。其实老板并没有太管我怎么拍,反而给了我非常大的自由。从小说改编到电影的时候,我因循自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做有关香港三、四十年代“塘西风月”的资料收集。原来的小说并没有把重点放在三、四十年代的香港,而是放在了梅艳芳饰演的如花在阴间等不到她的爱人,便去80年代的香港再去找她的爱人。剧本改编了以后,我把重点放到30年代如花与十二少的感情关系上面。我没有想商业不商业的问题,只是觉得这个电影需要对30年代有多一点的描写,有关如花和十二少一个是一个是贵公子的身份等等。结果到头来,不管评论也好,票房也好,《胭脂扣》都拿到蛮大的回报。
所以因有《胭脂扣》在先,嘉禾公司希望我再拍一次梅艳芳。我那个时候觉得梅艳芳的长相跟我一直喜欢看的三、四十年代一个默片的女演员阮玲玉有点像,就准备拍《阮玲玉》。但是后来因为个人的理由,梅艳芳推掉了,我便找来了张曼玉来演。但张曼玉长得不像阮玲玉,所以我就放弃去拍传统的人物传记片,而让张曼玉本人作为演员介入,比如加入了我跟她的访问,比如谈到她演阮玲玉。阮玲玉留下“人言可畏”的四字遗书之后自杀,但是张曼玉的态度跟阮玲玉所处三、四十年代不一样,她在九十年代和零零年代也有碰到这种娱乐新闻的炒作,张曼玉的态度是:“我管你,我谈恋爱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某种程度上,张曼玉在演阮玲玉的电影,也回顾了自己作为那个年代的时代女性,应该有自己坚持的态度。用这样一种形式来传达阮玲玉这个人物,也传达了张曼玉去演阮玲玉过程中女演员自己一些非常个人的感受。
下面这个问题不是问你自己的事情,我是就中国导演们的整体谈一下。有时候会有影评人或者评论界人士说,中国内地的一些导演是为了取悦外国观众拍的影片。我当然觉得这是无稽之谈了,我接触下来,多数的中国导演都对于外国观众知之甚少,对于外国的品位和发行制度都不是很了解。在香港,有人这样指责你吗?
其实香港电影新浪潮,像许鞍华这类的导演,是因为香港电影工业的商业性才会拍类型电影多一些。但是他们也有各自的风格和想说的故事,他们并没有想要卖给外国或者吸引到外国观众的初心。
反而他们的初心是非常纯粹的,比如我要拍一个悬疑电影,但是我更想在里面传达一个很动人的爱情故事。徐克的《蝶变》也好,《第一类型危险》也好,这些电影不商业吗?非常商业,但是他们有想要表达的内容。特别是许鞍华、谭家明、徐克这些导演,那时候的新浪潮电影能够让观众感受到,这些导演关注自己出生、长大、身处的城市空间,他们爱香港。其实他们的初心在这,对这座城市的关注,对这座城市的爱。
所以无论是做他们的副导演,或者说我自己做导演拍《女人心》《地下情》《胭脂扣》,我都愿意花一年多时间找资料,我都很想知道三、四十年代有“塘西风月”的香港跟我们身处的八、九十年代的现代香港有什么差别,以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等等。并没有说要讨外国观众喜欢,初心还是非常纯粹。
你的《胭脂扣》是根据一部很成功的小说改编的,最后也用了大演员,服务大公司,同时用有限的预算来完成了。但是我听说成片之后受到了干扰,是你挺身而出克服了困难,让它得以发行。
我当时是签给嘉禾电影公司的分公司威禾电影公司当导演,老板是成龙先生,他也是我的监制。像我刚刚说,我拍《胭脂扣》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但是后来整个做完后期成片后,成龙先生要自己去调影片检查一下。看完他觉得电影太闷了,让我好好考虑一下。
他说:“万梓良在电车上碰到梅艳芳的角色,并知道她是鬼的时候,一直冲到了电车前面的大玻璃窗,为什么他不就这样跳下来呢?这样你就可以用钢丝让万梓良从二楼的电车跳到地下。”梅艳芳还有一场戏是在路边摊认识了一个算命的觉得她是鬼,跟着她回家,并用法力把她打碎成七块。但是梅艳芳的功力更强,被打碎之后马上恢复,他说:“你没有考虑加一些比较商业的动作戏?”我说:“啊?这还是我拍的《胭脂扣》吗?成龙先生,要是你这样改的话,要不然你来做导演好了。”
当时你也讲到,希望跟梅艳芳合作拍《阮玲玉》。无论如何,是什么因素吸引着你对中国电影的历史如此感兴趣,可能你也是香港导演当中像这样的唯一一位。这是不是跟你拍香港早年的《胭脂扣》有关,所以你也自然而然关心三十年代老上海的风貌?我是恰好对中国电影史感兴趣的老外,我想了解一下,你对中国电影历史的这份执着和喜爱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要非常感谢香港电影中心,那是个非常小的地方。我年轻的时候还不能随便调到影片和胶片,我们就到电影中心非常小的房间里面,从电视上看录像带。这让我有机会看到早期三、四十年代的影片,甚至默片。包括我为什么喜欢阮玲玉,就是因为电影中心有很多阮玲玉留下来的影片。
除此以外,还有孙瑜导演、费穆导演,我认识这些导演都是因为香港电影中心和香港国际电影节。我们那时候有几个都喜欢电影的朋友,去电影节看完以后到香港大会堂面对着维港的海边聊电影,很晚都不愿意回家。某种程度上说,我对于中国电影史不能称得上是研究,更多的是喜爱。年轻的时候看邵氏、嘉禾的商业电影,没办法找到中国电影三、四十年代的那种精神和对人物的处理,那才是我非常喜欢的。
在1996年,电影百年的时候,英国电影协会找了全世界不同的导演来拍自己非常个人的对电影百年的经验。所以我便从小时候怎么跟父亲去澡堂、对父亲身体的迷恋等等讲起,拍摄纪录片《男生女相》。这也是对中国电影百年的回顾,但对我来讲,更多也是自己非常个人的,首次坦然面对观众谈到自己的性向选择。
她的确是广东人,她妈妈带着小时候的阮玲玉一起去到一个大户人家打工做女佣,所以她才认识到大户人家的公子张达民谈恋爱。我倒不觉得是因为同为广东人的渊源,更多的是我对阮玲玉这个人物感兴趣。包括带着她去打工的母亲,那种女性身体里面的强度。包括虽然最后她选择自杀是因为情感上的原因,但是我认为,她不愿意屈服于大环境对女性的一些评论和描写,是在用这种方式来反抗。
Q1:关导您好,我想问一下,在限制写作字数的情况下,对于塑造人物性格,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关锦鹏:我觉得初心还是很重要的。在创作上,我鼓励大家不要自我审查。除非你不碰这个人物或者题材,不然你在创作的时候会被一些无形的压力限制。你自己就先妥协,在剧本里做文章回避是最不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创作应该是没有限制的,你非讲不可,才会有一个好剧本,才是一部好电影的动力。
Q2:这几年,很多人说香港电影出不来很多新导演或者新的好剧本。想问一下,您觉得香港电影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以前黄金时代的样子,谢谢。
关锦鹏:我觉得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我现在在香港城市大学教书,跟一般学生谈到某部过去的一些电影,都没有几个人看过。我觉得那为什么还来选修编剧导演,感觉都没有那么爱电影,都不看电影。因为现在很多年轻观众都不愿意跑到电影院,觉得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跟看短视频相比,太花时间了。某种程度上,香港电影已经离开了八、九十年代黄金时代的投资资源。投资的资源有局限也是原因之一,影片类型变得非常个人化。对于这种电影,不光是海外的发行人,包括本地的观众也觉得,比起真的跑到电影院看,他情愿用手机、电脑上网。所以我觉得,客观原因是投资的大环境跟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不一样,也很难再回到那个状态了。但是我鼓励香港电影人应该努力,你个人想讲的故事是很重要,但是不要沉浸在里面。我常用八个字鼓励年轻导演:“既远扯近,既近扯远。”虽然到了自己非讲不可的状态,但是作为创作者,要退一步去检视自己的作品,代入观众的角度去看你自己的电影也很重要。
本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大师·对话”系列学术活动由劳力士ROLEX大力支持。
平遥国际电影展以“卧虎藏龙”为名,由展映、产业、学术、教育四大板块构成。在展映世界各国优秀影片的基础上,平遥国际电影展尤为注重发现并积极推广新兴及发展中国家青年导演的优秀作品,为这些影片提供发声的平台,旨在增强世界各国电影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以激活、繁荣世界电影的创作。